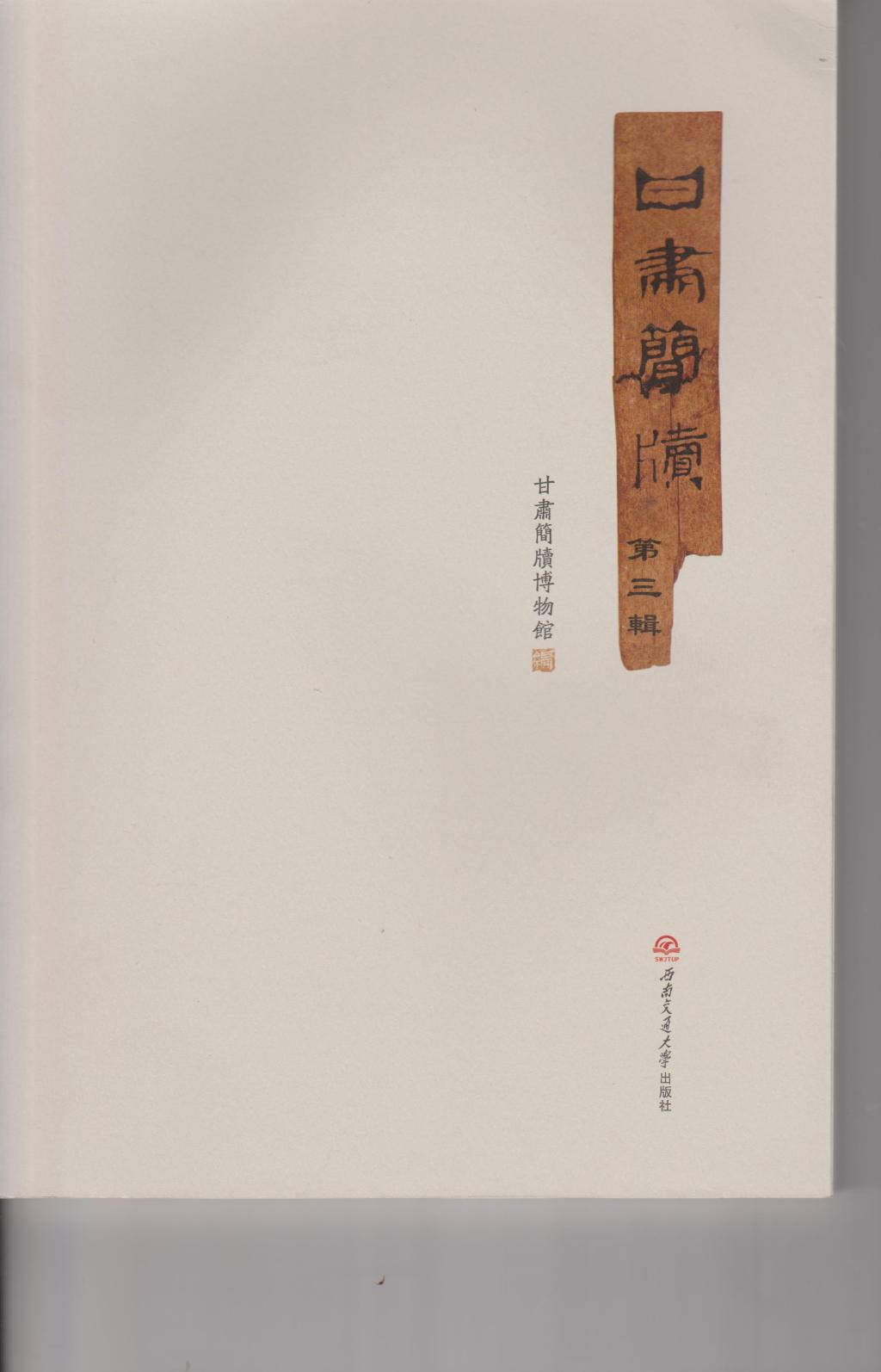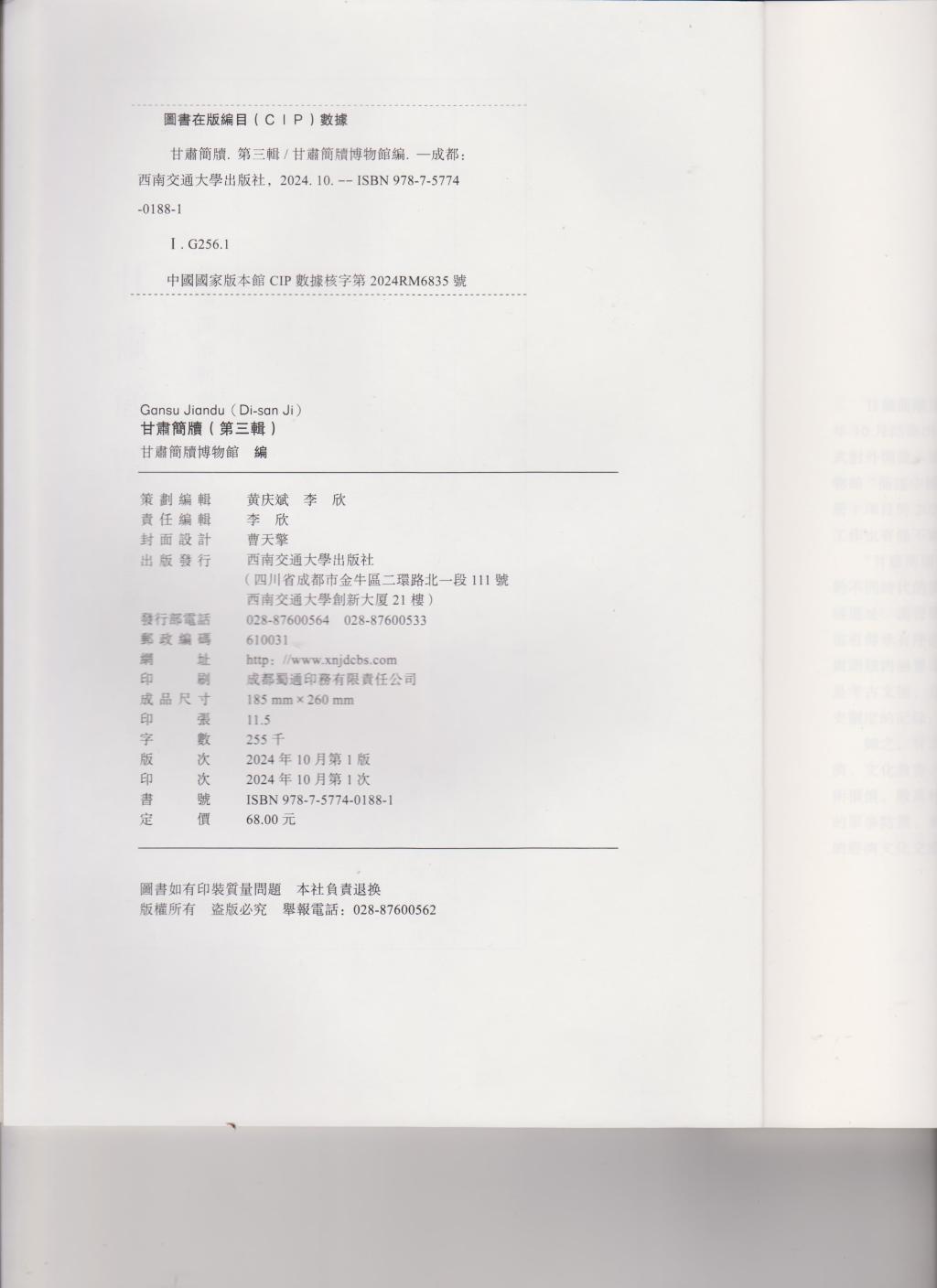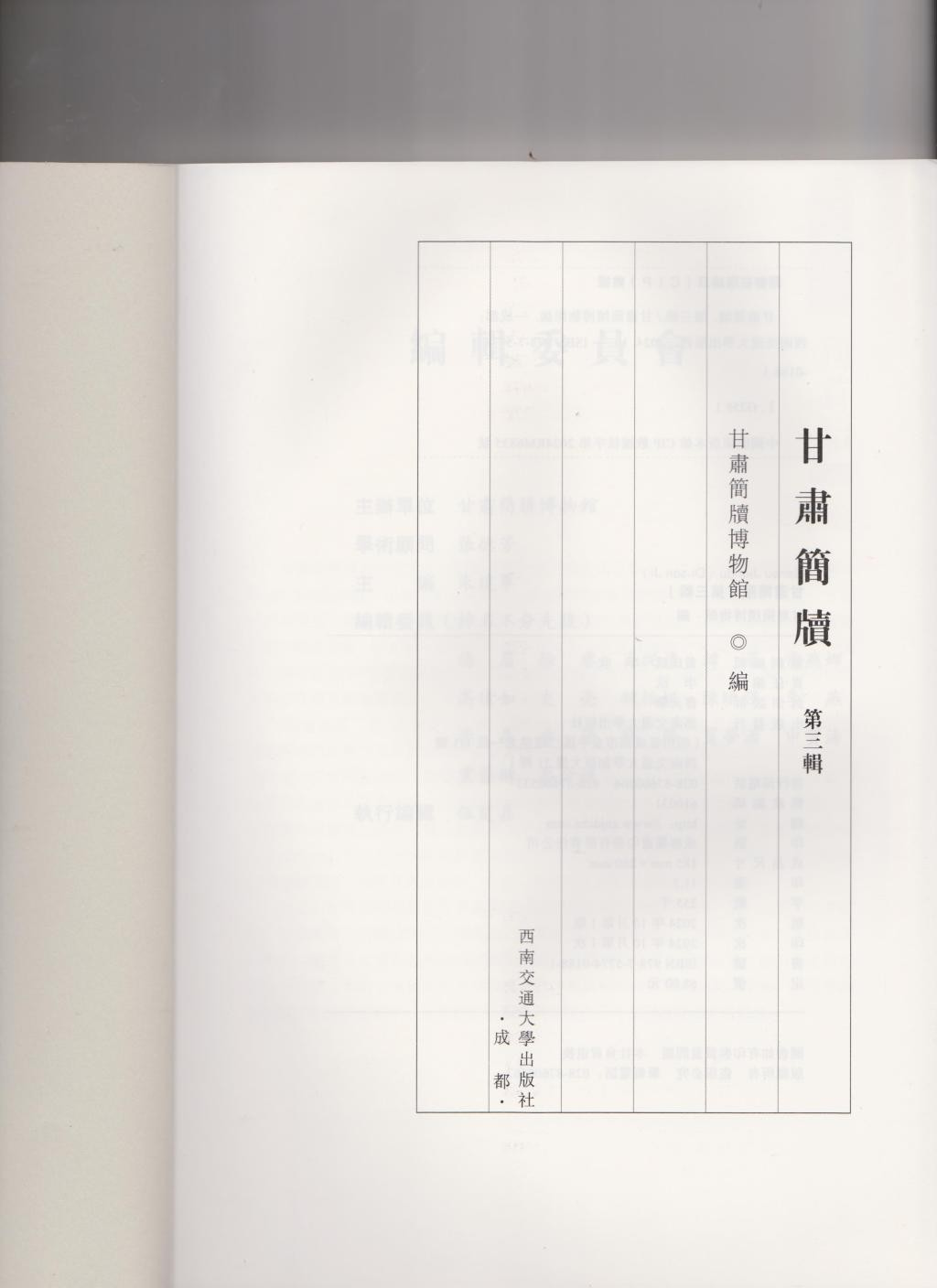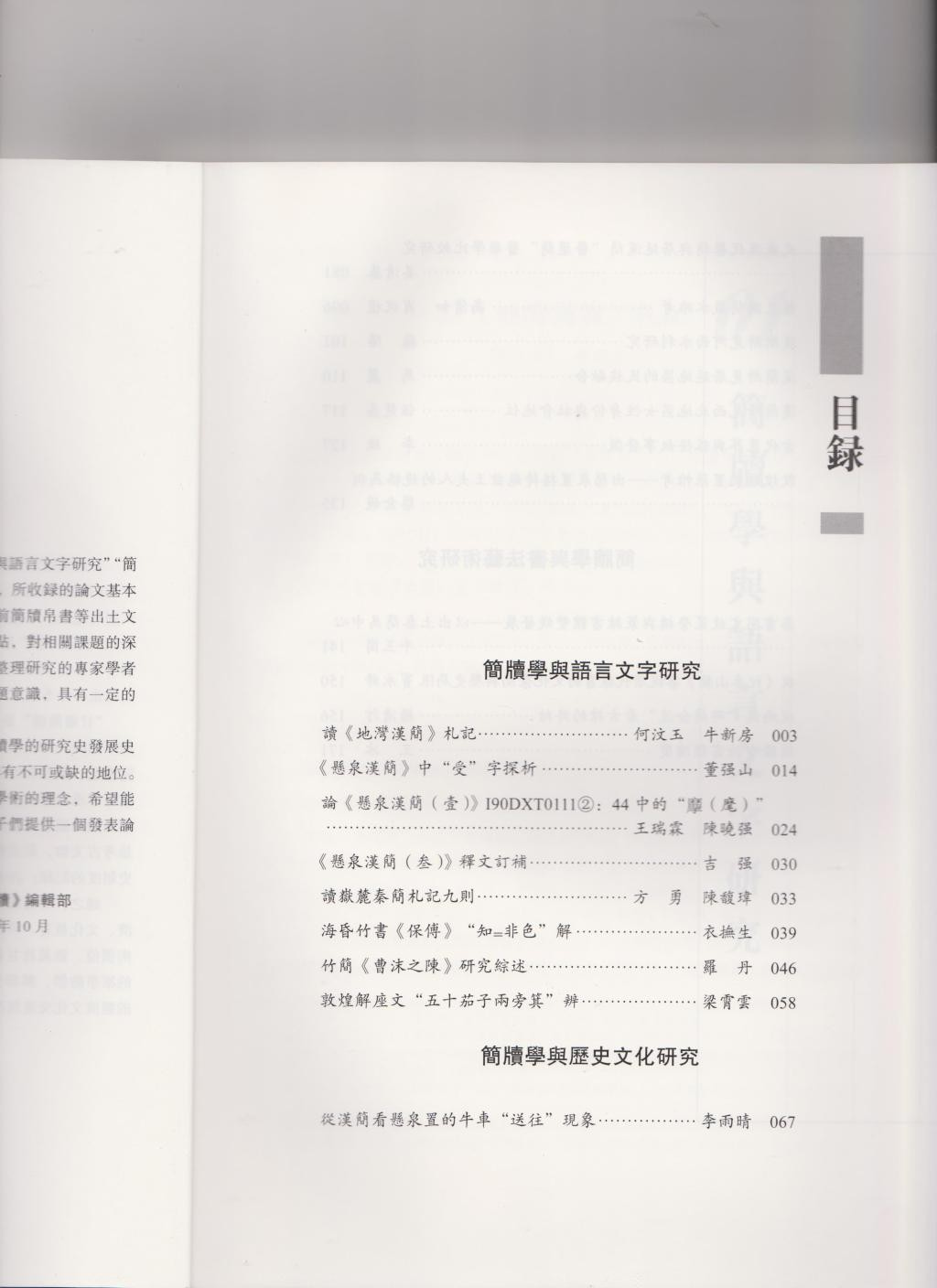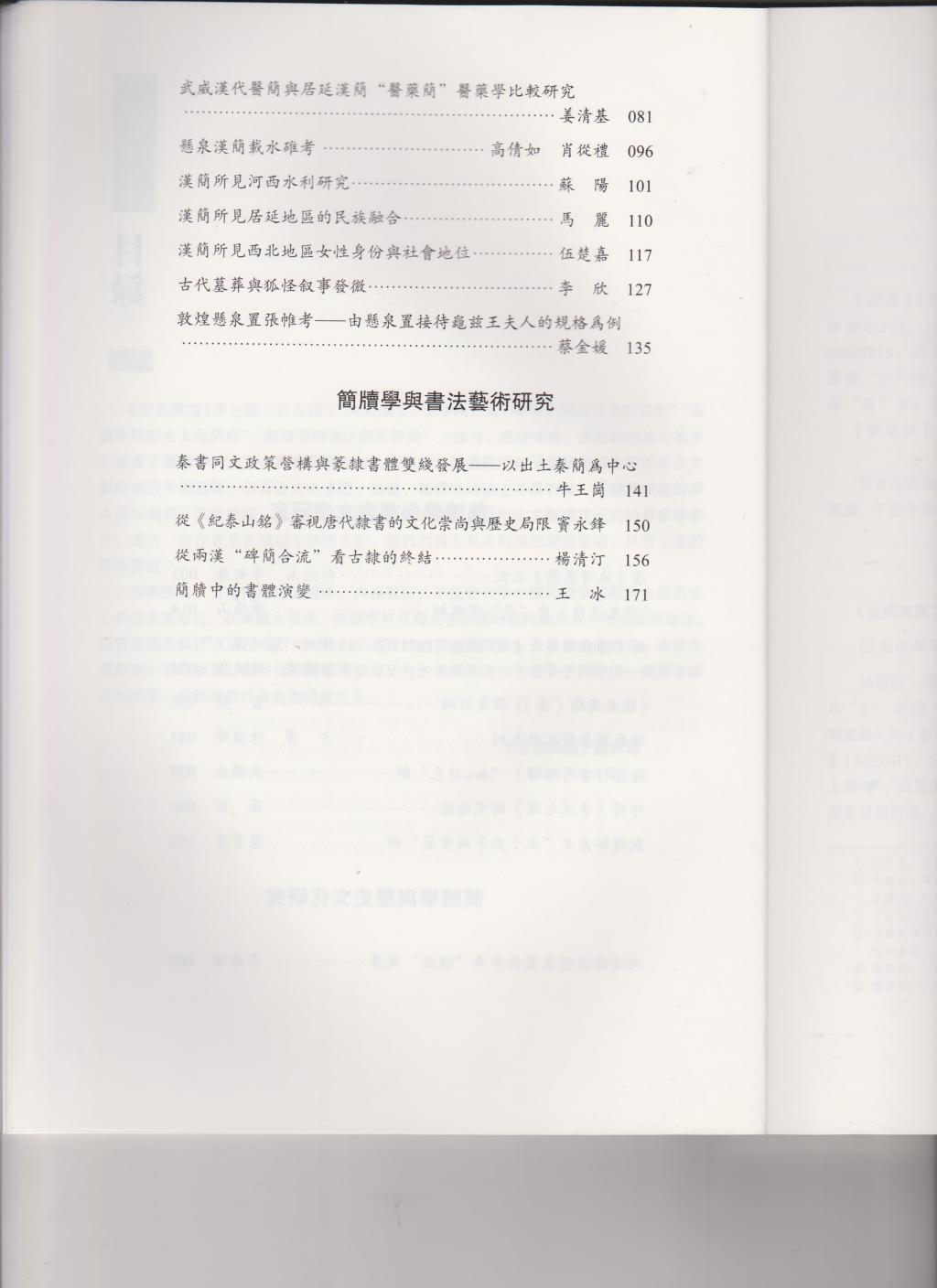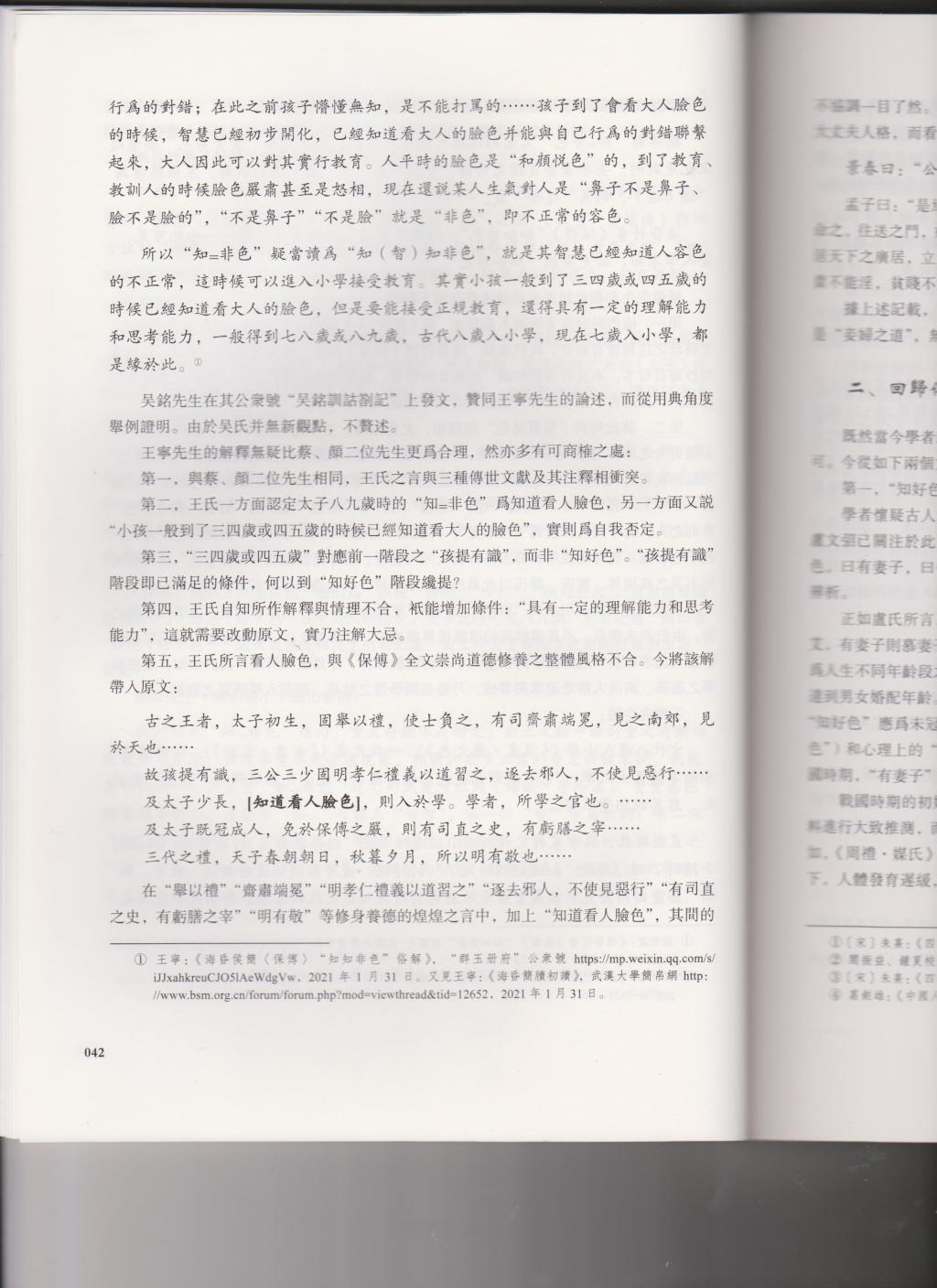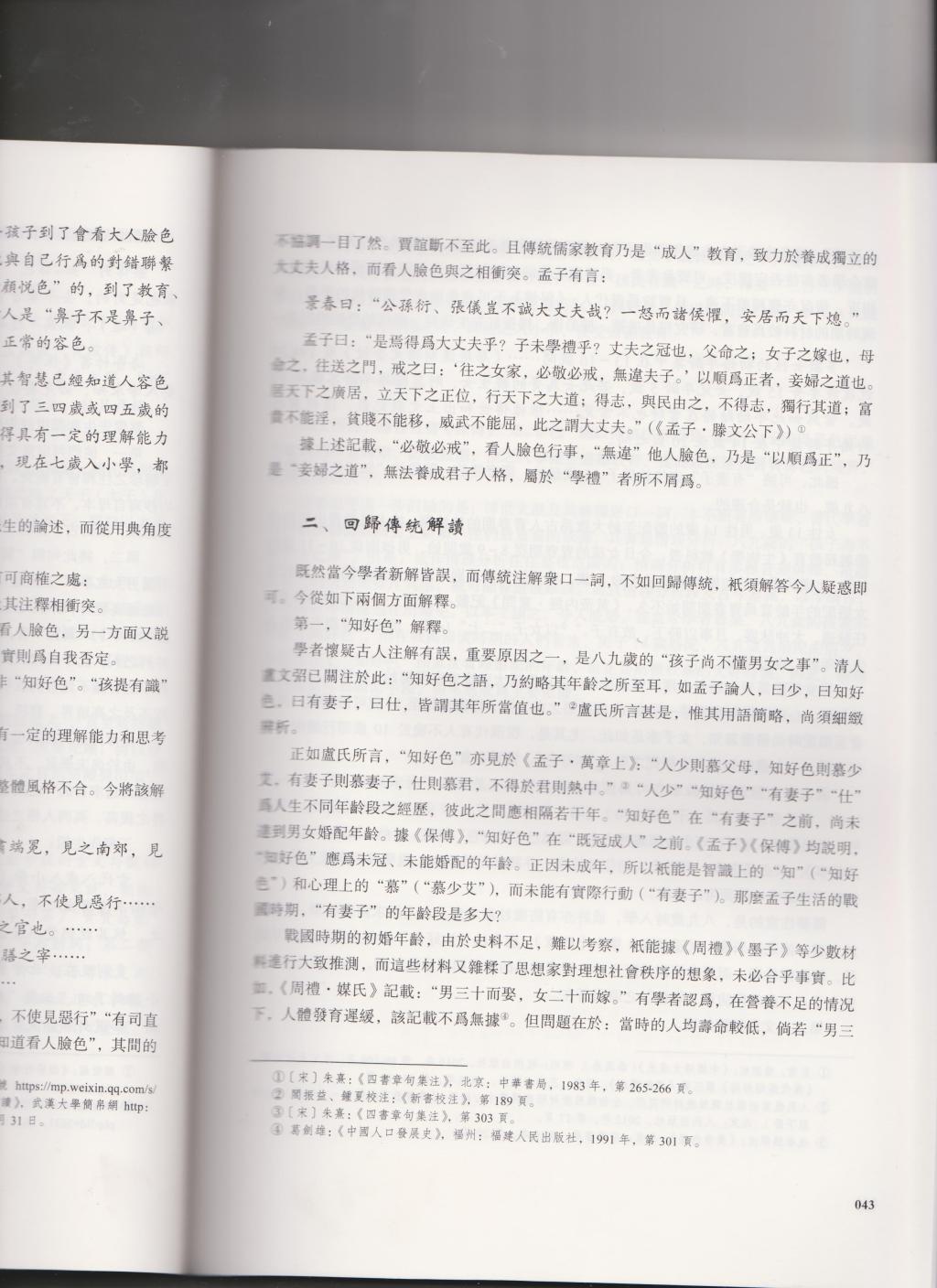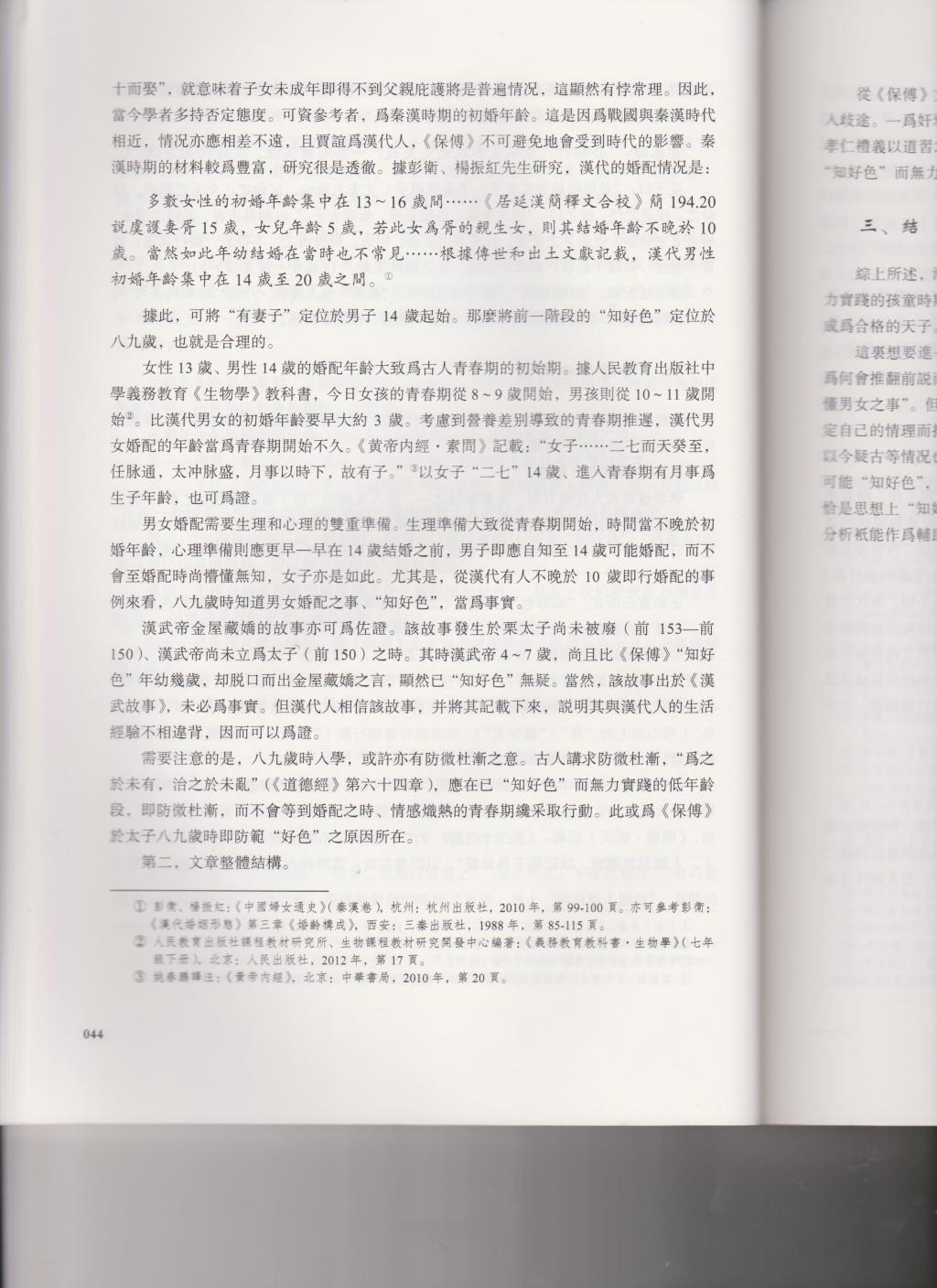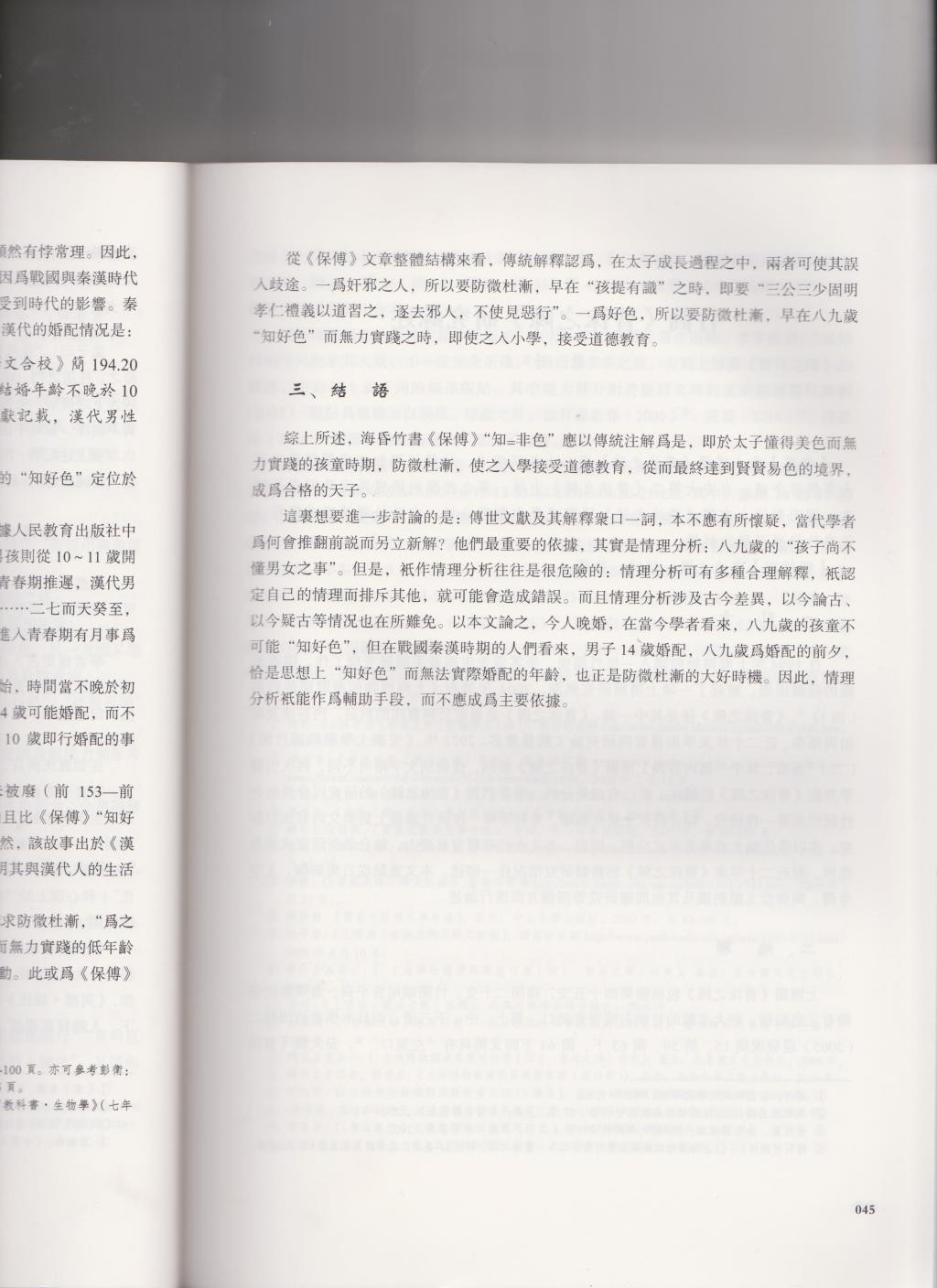近日,衣抚生副研究员在《甘肃简牍》(第三辑)发表论文《海昏竹书〈保傅〉“知=非色”解》。
摘要:海昏竹书《保傅》“知=非色”应遵传统文献,释为“知妃色”或“知好色”。“非”“妃”同音,可假借;“妃色”与“好色”可同义替换:对一般人而言,美色为“好色”,对太子而言,所娶为妃嫔,可言“妃色”。或疑八九岁之孩童未能“知妃(好)色”,然以《孟子》和古人初婚年龄证之,“有妻子”发生于男子14岁时,前此之“知妃(好)色”正为八九岁,并无可疑。正因“知妃(好)色”时年龄尚幼,只能是智识上的“知”和心理上的“慕”,而非实践上的“有妻子”。今人诸多新解皆误。
关键字:海昏竹书;《保傅》;知=非色;知好色;知妃色
引用格式:衣抚生:《海昏竹书〈保傅〉“知=非色”解》,甘肃简牍博物馆编:《海昏竹书〈保傅〉“知=非色”解》,成都: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,2024年,第39-45页。
一、问题的提出与学术史回顾
海昏竹书《保傅》可与贾谊《新书》、《大戴礼记》、《汉书》等传世文献对读,引起较多关注的,是“知=非色”一语。上述四种文献中的相关字句为:
天子少长,知=(知)非色,则入……(海昏竹书《保傅》)
及太子少长,知妃色,则入于小学。小者,所学之宫也。(《大戴礼记·保傅》)
及太子少长,知好色,则入于学。学者,所学之官也。(《新书·保傅》)
及太子少长,知妃色,则入于学。学者,所学之官也。(《汉书·贾谊传》)颜师古注:“妃色,妃匹之色。”
海昏竹书的“非”字与《大戴礼记》的“妃”字同音,可互相假借;《大戴礼记》《汉书》的“妃色”与《新书》的“好色”可同义替换:对一般人而言,美色为“好色”,对太子(天子)而言,所娶为妃嫔,可言“妃色”。因此,四种文献中的此语本意相同,颜师古注亦无不妥。清儒王聘珍《大戴礼记解诂》未出新注,显系相同见解无疑。今之学者于海昏竹书《保傅》刊布之后,却推翻前人经典解释,提出疑问与新解。
海昏竹简《保傅》的整理者韩巍先生说:
“知=(知)非色”,“知”下重文号当为误衍。“非色”,《大戴礼记》《汉书》皆作“妃色”;《新书》作“好色”,“好”当为“妃”之讹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颜师古注曰“妃色,妃匹”,似为望文生义的强解。疑海昏简作“非”当为本字,“妃”则是同音假借字。然而“非色”究竟应作何解?一时尚无好的想法,姑且存疑,以俟高明。
如前所述,“妃色”与“好色”可同义替换,颜师古注并非“强解”。那么,韩氏为何会将其断定为“望文生义的强解”?韩氏未作说明。笔者猜测,或因此时之天子(太子)年龄尚幼,并未婚配,韩氏因而疑其未能“知妃(好)色”。论述如下:贾谊以太子人生之成长阶段为写作顺序,今以《新书·保傅》为例进行说明:
古之王者,太子初生,固举以礼,使士负之,有司斋肃端冕,见之南郊,见于天也……故孩提有识,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,逐去邪人,不使见恶行……及太子少长,知好色,则入于学。学者,所学之官也。……及太子既冠成人,免于保傅之严,则有司直之史,有亏膳之宰……三代之礼,天子春朝朝日,秋暮夕月,所以明有敬也……
《保傅》从太子出生写起,继而为“孩提”时期、“少长”、“既冠成人”,直至最终继位为天子。“知妃(好)色”发生于入学前夕,太子此时年仅八九岁,未娶妃嫔,何以会“知妃(好)色”?这大概就是韩先生所疑之处。后文所引王宁先生之言则明确提出这一疑点。
蔡伟先生(网名抱小)提出新解:
我们认为“知=非色”这句,重文符号不是衍文。出土文献中误衍重文符号的现象并不少见,但这毕竟不是普遍现象,相对于众多正常的重文符号来说,祗能算作个例……但其实“知=非色”这句句式是可以同《论语·学而篇》“贤贤易色”联系起来的……海昏简“知=”可读为“智智”,第一个“智”字为动词;第二个“智”字为名词,智慧的意思。“智智”就是以智为智。“非”即“好丹非素”之“非”。“知=(知知-智智)非色”,是说崇尚智慧、鄙薄容色。也就是追求卓越,而不以表面容态为追求目的的意思。所以就要入学学习,这样才可使内心丰盈。
颜世铉先生基本赞同蔡伟先生的主张,而对“色”字进行新解:
蔡伟对“知=非色”文意的理解大致是可信的,而把它和“贤贤易色”联系起来也是对的。去年笔者曾撰文讨论“贤贤易色”的“易”字的训解,主张应读为“逷(逖)”,训为“远离”义。
海昏竹书《保傅》“知知非色”,指亲近智者、远离美色之意……由此可见,要入学求知,必先要能“知知非色”。
蔡伟先生和颜世铉先生的论述存在如下问题:
第一,他们判定重文符号不为误文,与《新书》、《大戴礼记》、《汉书》之记载及颜师古、王聘珍之注释皆有冲突。我们须知,海昏竹书《保傅》与此三种文献为同一来源,且四者均为抄写母本,不宜有两种解读,而该文的作者、编者均为同时代之人,恐不至连简单抄写都错,颜师古、王聘珍等大儒亦未必读不懂此类简单字句。
第二,将此句与“贤贤易色”相关联,尤为错谬。王宁先生批评说:“这时候孩子尚不懂男女之事。”王氏之言并不准确,下文将进行评述。其实,真正的问题是:“贤贤易色”乃是极高境界,断非八九虚岁的孩童所能达到。孔子有言: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“贤贤”者,“好德”也;“易色”者,不“好色”也。将“好德”与“好色”并列之人,孔子尚且评价为“吾未见”,何况是“好德”而不“好色”、“贤贤易色”之人?孔子之言虽不免有为说明其难而略有夸大的可能性,然亦足以说明“贤贤易色”实为常人所不及之高境界。颜氏以此为孩童入学条件,未免强人所难。
相较之下,蔡伟先生以“容色”“容态”为解,更为通达,但亦有问题:太子入小学之前,由于尚未学习,不具备较高的道德境界与追求。蔡伟先生以“追求卓越,而不以表面容态为追求目的”之高标准为孩童入小学的前提条件,亦为强人所难。我们须知,道德境界之提高、高尚人格之追求与养成,乃是长期学习之结果,而非入学学习之前提。
王宁先生说:
古代八岁入小学(《汉书·艺文志》),一说九岁(《新书·容经》),这时候孩子尚不懂男女之事,“色”解释为美色恐怕不确当,抱小先生解释为“容色”当近之,然其说仍觉不安。
直到现在,北方农村父母教育小孩还经常是“棍棒教育”,打骂常有。但要到小孩到了四、五岁“知道好赖脸儿了”的时候,纔可以开始这么教训、教育。所谓“知道好赖脸儿”就是会看大人脸色的好坏知道大人的喜怒,并因此知道自己行为的对错;在此之前孩子懵懂无知,是不能打骂的……孩子到了会看大人脸色的时候,智慧已经初步开化,已经知道看大人的脸色并能与自己行为的对错联系起来,大人因此可以对其实行教育。人平时的脸色是“和颜悦色”的,到了教育、教训人的时候脸色严肃甚至是怒相,现在还说某人生气对人是“鼻子不是鼻子、脸不是脸的”,“不是鼻子”、“不是脸”就是“非色”,即不正常的容色。
所以“知=非色”疑当读为“知(智)知非色”,就是其智慧已经知道人容色的不正常,这时候可以进入小学接受教育。其实小孩一般到了三四岁或四五岁的时候已经知道看大人的脸色,但是要能接受正规教育,还得具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思考能力,一般得到七八岁或八九岁,古代八岁入小学,现在七岁入小学,都是缘于此。
吴铭先生在其公众号“吴铭训诂札记”上发文,赞同王宁先生的论述,而从用典角度举例证明。由于吴氏并无新观点,不赘述。
王宁先生的解释无疑比蔡、颜二位先生更为合理,然亦多有可商榷之处:
第一,与蔡、颜二位先生相同,王氏之言与三种传世文献及其注释相冲突。
第二,王氏一方面认定太子八九岁时的“知=非色”为知道看人脸色,另一方面又说“小孩一般到了三四岁或四五岁的时候已经知道看大人的脸色”,实则为自我否定。
第三,“三四岁或四五岁”对应前一阶段之“孩提有识”,而非“知好色”。“孩提有识”阶段即已满足的条件,何以到“知好色”阶段纔提?
第四,王氏自知所作解释与情理不合,祗能增加条件:“具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思考能力”,这就需要改动原文,实乃注解大忌。
第五,王氏所言看人脸色,与《保傅》全文崇尚道德修养之整体风格不合。今将该解带入原文:
古之王者,太子初生,固举以礼,使士负之,有司斋肃端冕,见之南郊,见于天也……
故孩提有识,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,逐去邪人,不使见恶行……
及太子少长,[知道看人脸色],则入于学。学者,所学之官也。……
及太子既冠成人,免于保傅之严,则有司直之史,有亏膳之宰……
三代之礼,天子春朝朝日,秋暮夕月,所以明有敬也……
在“举以礼”“斋肃端冕”“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”“逐去邪人,不使见恶行”“有司直之史,有亏膳之宰”“明有敬”等修身养德的煌煌之言中,加上“知道看人脸色”,其间的不协调一目了然。贾谊断不至此。且传统儒家教育乃是“成人”教育,致力于养成独立的大丈夫人格,而看人脸色与之相冲突。孟子有言:
景春曰:“公孙衍、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?一怒而诸侯惧,安居而天下熄。”
孟子曰:“是焉得为大丈夫乎?子未学礼乎?丈夫之冠也,父命之;女子之嫁也,母命之,往送之门,戒之曰:‘往之女(汝)家,必敬必戒,无违夫子。’以顺为正者,妾妇之道也。居天下之广居,立天下之正位,行天下之大道;得志,与民由之,不得志,独行其道;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此之谓大丈夫。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
据上述记载,“必敬必戒”,看人脸色行事,“无违”他人脸色,乃是“以顺为正”,乃是“妾妇之道”,无法养成君子人格,属于“学礼”者所不屑为。
二、回归传统解读
既然当今学者新解皆误,而传统注解众口一词,不如回归传统,只须解答今人疑惑即可。今从如下两个方面解释:
第一,“知好色”解释。
学者怀疑古人注解有误,重要原因之一,是八九岁的“孩子尚不懂男女之事”。清人卢文弨已关注于此:“知好色之语,乃约略其年龄之所至耳,如孟子论人,曰少,曰知好色,曰有妻子,曰仕,皆谓其年所当值也。”卢氏所言甚是,惟其用语简略,尚须细致辨析。
正如卢氏所言,“知好色”亦见于《孟子·万章上》:“人少则慕父母,知好色则慕少艾,有妻子则慕妻子,仕则慕君,不得于君则热中。”“人少”“知好色”“有妻子”“仕”为人生不同年龄段之经历,彼此之间应相隔若干年。“知好色”在“有妻子”之前,尚未达到男女婚配年龄。据《保傅》,“知好色”在“既冠成人”之前。《孟子》《保傅》均说明,“知好色”应为未冠、未能婚配的年龄。正因未成年,所以祗能是智识上的“知”(“知好色”)和心理上的“慕”(“慕少艾”),而未能有实际行动(“有妻子”)。那么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,“有妻子”的年龄段是多大?
战国时期的初婚年龄,由于史料不足,难以考察,只能据《周礼》《墨子》等少数材料进行大致推测,而这些材料又杂糅了思想家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想象,未必合乎事实。比如,《周礼·媒氏》记载:“男三十而娶,女二十而嫁。”有学者认为,在营养不足的情况下,人体发育迟缓,该记载不为无据。但问题在于:当时的人均寿命较低,倘若“男三十而娶”,就意味着子女未成年即得不到父亲庇护将是普遍情况,这显然有悖常理。因此,当今学者多持否定态度。可资参考者,为秦汉时期的初婚年龄。这是因为战国与秦汉时代相近,情况亦应相差不远,且贾谊为汉代人,《保傅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的影响。秦汉时期的材料较为丰富,研究很是透彻。据彭卫、杨振红先生研究,汉代的婚配情况是:
多数女性的初婚年龄集中在13—16岁间……《居延汉简释文合校》简194.20说虞护妻胥15岁,女儿年龄5岁,若此女为胥的亲生女,则其结婚年龄不晚于10岁。当然如此年幼结婚在当时也不常见……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记载,汉代男性初婚年龄集中在14岁至20岁之间。
据此,可将“有妻子”定位于男子14岁起始。那么将前一阶段的“知好色”定位于八九岁,也就是合理的。
女性13岁、男性14岁的婚配年龄大致为古人青春期的初始期。据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义务教育《生物学》教科书,今日女孩的青春期从8-9岁开始,男孩则从10-11岁开始。比汉代男女的初婚年龄要早大约3岁。考虑到营养差别导致的青春期推迟,汉代男女婚配的年龄当为青春期开始不久。《黄帝内经素问》记载:“女子……二七而天癸至,任脉通,太冲脉盛,月事以时下,故有子。”以女子“二七”14岁、进入青春期有月事为生子年龄,也可为证。
男女婚配需要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准备。生理准备大致从青春期开始,时间当不晚于初婚年龄,心理准备则应更早——早在14岁结婚之前,男子即应自知至14岁可能婚配,而不会至婚配时尚懵懂无知,女子亦是如此。尤其是,从汉代有人不晚于10岁即行婚配的事例来看,八九岁时知道男女婚配之事、“知好色”,当为事实。
汉武帝金屋藏娇的故事亦可为佐证。该故事发生于栗太子尚未被废(前153年—前150年)、汉武帝尚未立为太子(前150年)之时。其时汉武帝4—7岁,尚且比《保傅》“知好色”年幼几岁,却脱口而出金屋藏娇之言,显然已“知好色”无疑。当然,该故事出于《汉武故事》,未必为事实。但汉代人相信该故事,并将其记载下来,说明其与汉代人的生活经验不相违背,因而可以为证。
需要注意的是,八九岁时入学,或许亦有防微杜渐之意。古人讲求防微杜渐,“为之于未有,治之于未乱”(《道德经》第六十四章),应在已“知好色”而无力实践的低年龄段,即防微杜渐,而不会等到婚配之时、情感炽热的青春期纔采取行动。此或为《保傅》于太子八九岁时即防范“好色”之原因所在。
第二,文章整体结构。
从《保傅》文章整体结构来看,传统解释认为,在太子成长过程之中,两者可使其误入歧途。一为奸邪之人,所以要防微杜渐,早在“孩提有识”之时,即要“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,逐去邪人,不使见恶行”。一为好色,所以要防微杜渐,早在八九岁“知好色”而无力实践之时,即使之入小学,接受道德教育。
三、结语
综上所述,海昏竹书《保傅》“知=非色”应以传统注解为是,即于太子懂得美色而无力实践的孩童时期,防微杜渐,使之入学接受道德教育,从而最终达到贤贤易色的境界,成为合格的天子。
这里想要进一步讨论的是:传世文献及其解释众口一词,本不应有所怀疑,当代学者为何会推翻前说而另立新解?他们最重要的依据,其实是情理分析:八九岁的“孩子尚不懂男女之事”。但是,祗作情理分析往往是很危险的:情理分析可有多种合理解释,祗认定自己的情理而排斥其它,就可能会造成错误。而且情理分析涉及古今差异,以今论古、以今疑古等情况也在所难免。以本文论之,今人晚婚,在当今学者看来,八九岁的孩童不可能“知好色”,但在战国秦汉时期的人们看来,男子14岁婚配,八九岁为婚配的前夕,恰是思想上“知好色”而无法实际婚配的年龄,也正是防微杜渐的大好时机。因此,情理分析只能作为辅助手段,而不应成为主要依据。